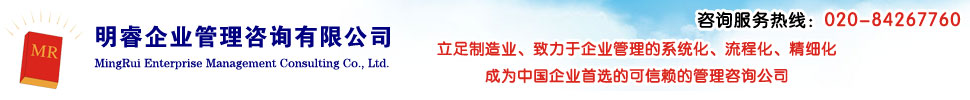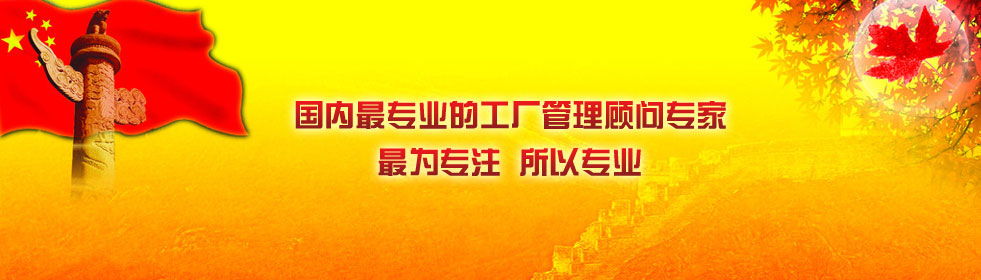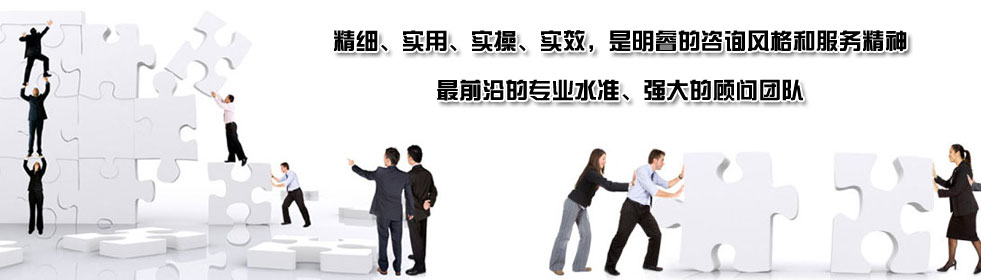領導者在做決策時,有時會遇到兩個誓不兩立的對立物突然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這時候,應當學會從對立中尋求轉機,這是引導你走出決策困境的正確思維方法。
這種決策思維的規范表述是:從看似對立的無法“調和”的兩個事物之間,深刻認識它們的相互關系,從中尋找此消彼長或者此長彼消的轉機,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顯然,這種決策思維,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
一部《孫子兵法》,幾乎從頭至尾都在講如何從對立中尋求轉機。在你死我活的軍事斗爭中,充滿著尖銳的矛盾和對立的因素。敵與我,強與弱,進與退,攻與守,勝與敗,多與少,虛與實,勞與逸,內與外,奇與正, 勇與怯,治與亂,遠與近,安與危,……這些看似對立的事物,無時無刻不在運動變化著,并且時常出現互相轉化的趨勢。只要決策者能夠運用辯證思維,既看到事物內部的矛盾關系,又看到對立雙方的轉化趨勢和轉化時機,積極創造轉化條件,就能從對立中尋求到解決問題的轉機,確保決策行為取得理想的結果。
從對立中尋求轉機的辯證思維,其思維軌跡往往穿行于兩個互相對立的事物之間,形成一條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曲線。軍事家為了麻痹、迷惑敵人, 往往“虛而示之以實”,或者“實而示之以虛”。當敵人已經掌握了你這套用兵謀略時,決策者的思維軌跡便適時地螺旋上升,又轉向對立的另一方去尋求轉機,采取極端的形式,以違反常理的辦法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這就是 “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為實。”“實而實之,使敵轉疑以我為虛。” (《張宇》)如諸葛亮命令關羽在小路上設伏,又故意在小路上點起煙火,結果銹使在赤壁失敗的曹操中計。后來,諸葛亮又施空城計嚇得敵軍不敢進城。這些案例,都是古代領導人才靈活巧妙地運用辨證思維從對立中尋求轉機的成功實踐。
對立因素之間的聯系,是十分復雜的。對立雙方的轉化,往往是有條件的,而決非無條件的。只有當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立雙方確實具備轉化的條件時,促使事物向著對立方問轉化,才成為可能。這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轉機”。在這一思維過程中,領導者的決策思維是否正確,關鍵在于看他能否把根對立雙方的轉化規律,及時捕捉轉化時機,積極創造轉化條件。倘若做不到這一點,那么, 一味想從對立中尋找轉機的企圖就會落空,甚至將領導者引上錯誤決策的歧途。在現實生活中.此類例子屢見不好鮮。即使是—些深孚眾望的杰出領導人才,也難免在這方面產生失誤,在事關大局的戰略決策中,準確把握對立雙方的轉化規律,捕捉轉化時機,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頗具風險的。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決策的重大失誤。
那么,從對立中尋求轉機.領導者需要注意哪些要點呢?作者以為,至少應注意以下6點:
(1)當對立雙方正處于相對穩定的僵持階段時,領導者應當清醒地看到,此時無論哪一方,都不可能迅速朝著對立方向轉化。此時領導者需要做的,不是如何忙于捕捉轉化時機,而是如何積極創造轉化條件。
(2)當對立雙方中的某一方,正朝著自己的同一方向繼續發展變化時(諸如亂者更亂,弱者更弱……),領導者切勿發生“誤診”,誤以為通過采取極端手段,讓亂者“亂”個痛快,弱者“弱”個徹底,事物的轉機就會到來。那樣做,往往會適得其反,進一步加劇事態的惡化。這時候,領導者唯一的正確抉擇,就是如何抑制對立中的某—方繼續朝著自己的同一方向發展。唯有這樣,才有可能從中創造轉化條件,進而捕捉到轉化時機。
(3)當客觀形勢需要領導有從對立雙方中選擇某一方時,領導者切忌左右據擺或矯枉過正,前者會使你失去轉機,而后者則將使你走上錯誤的極端。兩者盡管“病癥”有所不同,但“病根”卻是—個;都是由封閉的小生產生活環境中產生的狹隘心理誘發的。因而在許多時候,這兩種“病癥”會互相轉化,交替發生。諸如,在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方面,某些領導者總是在右或“左”這兩個極端上進行大幅度搖擺;在對外關系方面,有些人好走排外或媚外這兩個極端。當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正在征糾正某一種傾向時,又掩蓋了另一種傾向……對于上述這些不良思維習慣,領導者應該有意識地予以克服。
(4)當對立雙方看似“誓不兩立”,絕無調和余地的時候,領導者應出冷能地透過表象去剖析事物的本質,堅信即使是尖銳對立的雙方,也是有共些共同點的。離雙方的接合部越近,這種共同點就越多。按照這一思維軌跡去尋找能被雙方共同接受的東西,往往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轉機。例如: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在生產力方面有共同點,即使在社會管理制度的某些具體方面也同樣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表現在:在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方式上,盡管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體不同,但在非主體部分以及主體經濟的組織形式上,諸如企業管理體制、兩權分離形式、股份制、租賃制等等,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政治制度人雖然國體有本質區別,但在政體方面,如選舉制度、司法體制、文官制度等,也有不少類似之處;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由于找到了這么多的共同點,我們才能有把握地說,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有選擇地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先進的管理方式和科學文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顯而易見,從這種對立雙方中尋找“共同點”的思維方式,有時候(不是任何時候)確實能幫助領導者很快捕捉到解決問題的轉機。
(5)當對立雙方一時很難找到共同點時,有時候,領導者不必忙于做出有利于某一方的抉擇,也不必強行讓某—方向別一方的立場靠攏。比較穩妥的辦法是:盡量比對立雙方同時向近接雙方的“直線”上的某一點靠攏。這—點,不一定是“直線”上的“中點”,只要雙方都能做出某種妥協和讓步,達一事實本身,就能促使對立雙方找到一種“體面”地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是從對立中尋找轉機的又一種思維模式。
(6)根據“此消彼長”的事物轉化規律。當對立雙方出現不利于決策者的轉化趨勢時,為了阻讓事態的近一步惡化,決策者不妨采取適度削弱“得勢”的一方,同時又適度增強“失勢”的一方的策略,來重建對大雙方的均勢。在某些情況下,解決問題的轉機,往往就存在于對立雙方的均勢之小。
決策思維的高明與否,正確與否,主要就體觀在它能否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以“智”取勝上。從對立中尋求轉機的辨證思維,是最復雜、最多變的一種決策思維,它的發展格局變幻莫測,往往很難控制和駕馭。我們在這里陳述的思維軌跡,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描述,理性的概括,它只能供有志于闖這一難關的領導者參考。更巧妙、更實用的決策思維軌跡,還有待于各級領導者在自己的實踐中摸索、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