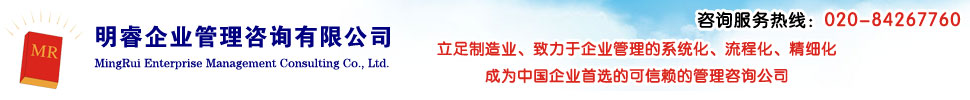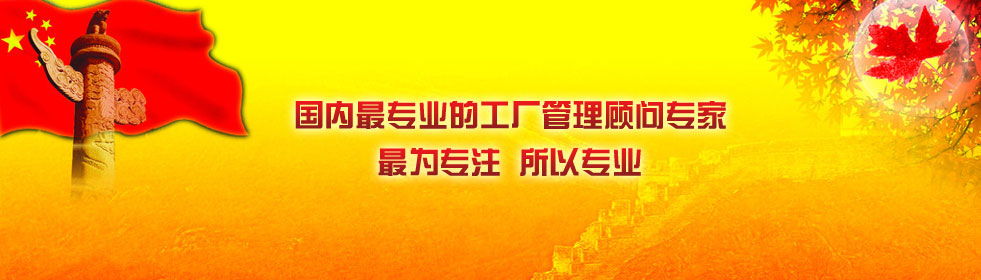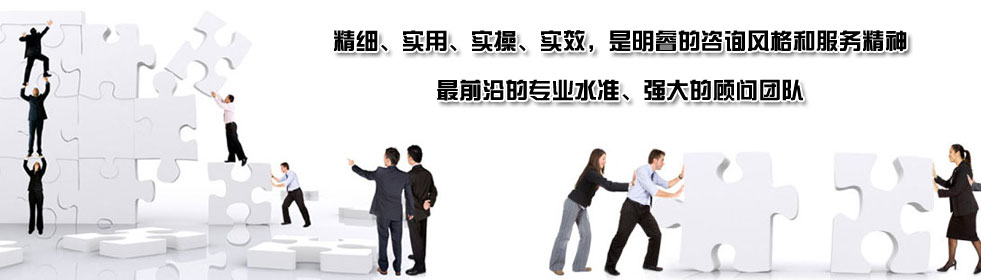誰能幫幫我---高稅負,企業家心中永遠的痛
女企業家痛哭稱太難撐不下去了
轉載
如果把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圖看成中國經濟的體檢表,那么其中一個陡然向下的箭頭不得不引起注意。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8.3%,有媒體稱,這個數字創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9%,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稱“斷崖式下跌”。
民營企業怎么了?“不能光看宏觀政策如何,還要聽民營企業家的真實感受。”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決定走到企業家中間去聽一聽、看一看。
2016年年初,他與中國社科院教授馮興元發起了“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研究”的調研,歷時近一年,專家課題組團隊先后赴貴陽、武漢、杭州、大連等4個城市的民營企業中進行調查。
政府頻出招為企業減負
事實上,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為企業減負已成為共識。這一點,從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見清晰的政府意圖及減負誠意,“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于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不同于以往的“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2016年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承諾“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目的是要幫助企業家們把口袋里的真金白銀省下來。
按照預計,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等政策將直接給企業和個人卸下一年5000多億元的負擔;同時,國務院決定從5月1日起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加上此前已經降低的其他費率,預計每年可降低企業成本1200億元以上。
一系列減稅清費的政策下,中國宏觀稅負在經歷一段時期上升之后,穩定在29%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2014年、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均為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當然,稅負高低,因為統計口徑不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
李煒光把2005年~2014年10年間中國稅收收入按照企業類型來分析,發現一個現象,在總稅收逐年攀升的趨勢下,國有企業的稅收貢獻率整體呈下降趨勢,而非公經濟稅收貢獻率卻在持續上升,特別是2009年以后,幾乎一年一個臺階,由2.75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萬億元,占比達到51.43%。于是,他把注意力逐漸集中在民營企業群體上。
座談會變成了“訴苦會”
李煒光發現,關注民營企業生存狀況的調查不多,且大多是官方發起的。他想搞一次 “老百姓“自己的調研”。
為此,這次由多名學者發起的調研不能只有程式化的調查問卷和冷冰冰的數字統計,請民營企業家和學者一起座談聊天“聽聽真心話”,是調研過程中很重要的環節。
令李煒光驚訝的是,座談會常常變成“訴苦會”。一位在商界摸爬滾打近20年的女企業家談到經營多年的企業,最多再撐一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忍不住失聲痛哭,“感覺太難了,實在撐不下去了。”
這是一家已具有相當規模、生產起重設備的機械制造企業,也是經濟下行中受影響最大的一類企業。李煒光說:“在這波經濟下行的大潮中,規模大、造價高、重資產的制造類企業受沖擊非常大,其中重工業受摧殘最甚。”
為了保住自己苦心經營十幾年的企業,這位女老板把所有的積蓄都投入進去,還因為一心撲在企業上忽略了家人,“把家都犧牲了,卻什么也沒給自己留下。”
更讓她愧疚的是,為了企業轉型發展,她把海外留學后在國外大公司擁有高薪職位的女兒叫回國幫忙,“當初是我命令她回來,承諾給她每個月1萬~2萬元薪水和家族企業的美好前景,可現在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女企業家的哭訴并非個例。
參與調研的民營企業分布在中國的東、中、西及東北四大區域,杭州、武漢、貴陽和大連作為各區域的代表城市,基本上每個地區至少調研30個企業,覆蓋了國家統計局劃分的12個大行業,“不能說代表整個中國,但確實有一定典型性”。
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苦苦硬撐,有的靠偷稅漏稅茍延殘喘,有的把資產轉到國外,留在國內的企業成了空殼。這種情況在華北地區有不少,東北和中部地區更多。
李煒光與企業家們接觸后深切地感到,在經濟下行期,很多民營企業家受到沖擊。“如果民營企業家群體感覺看不到希望,對中國經濟發展將很不利。”李煒光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必須要靠人而不是靠錢堆起來。
87%的企業家感覺稅負很重和較重
民企經營難與稅負有多大關聯?李煒光畫了兩根V型線,以便讓問題的癥結清晰可見。
他選擇1978年至2015年,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段分析中國經濟發展脈絡。在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其中一根代表中國整體GDP走勢的線,其間有過幾次波峰起伏,但大致走向如同倒過來的V字;而另一根代表企業宏觀稅負的線,呈現正V字的走勢。
正反兩個V疊在一起反映了當下企業的境遇:在經濟下行趨勢下,較重的宏觀稅負成為企業“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說用數字表達稅負高低,是一種客觀呈現;那么談到稅負輕重,往往摻雜了更多主觀感受,被稱為“企業稅負痛感”,也就是說,同樣繳10個點的稅,有的覺得還行,有的則感覺撐不下去了。
占中國企業9成以上的民營企業,稅負痛感更強,這在調研中的幾組數據里顯露無遺:87%的企業家認為稅負很重和較重,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而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反映出我國總體稅負水平可能已經嚴重拖累了企業經營。”
那么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是多少呢?按照新的“四本預算”的算法,去除其中重疊的部分,大體在37%左右,而目前政府稅收收入的90%以上是由企業繳納的,正如稅務專家指出的,我國企業稅負與宏觀稅負之間有高達90%的相似度。
另外,企業稅負也可以用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數中的“企業總稅率”來衡量。所謂“總稅率”,指的是企業稅收和各種強制性繳費,包括所得稅、勞務稅(五險一金)、轉嫁不出去的流轉稅負擔,以及其他各種稅費占商業凈利潤的比例。
在中國,企業總稅率在2012年以前大體處于世界中等水平,2012年至2013年間驟然上升,這之后3年的總稅率分別是68.7%、68.5%和67.8%,逐年微有下降,但處于世界高水平,高于高收入國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16年的數據目前已公布,中國重回68%,說明今年以來為企業減輕稅費負擔的努力成效有限。
查看2016年中國總稅率68%的具體構成,其中10.8%為利得稅、48.8%為勞務稅、10.8%為其他稅;由此可見,占比較大稅費負擔為勞務稅,即公司作為雇主為雇員配套繳納的“五險一金”支出,在2016年,是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
李煒光說,目前在我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不過10%上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稅費占比足可以讓大多數民營企業陷入困境,“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原因。”
第二產業稅負大大超過第三產業。調研組成員臧建文調研時有一個明顯的感受,網店和實體店稅負嚴重不均,同樣是經營主體,對于“互聯網+”時代快速興起的電商,我國尚未健全稅制。在杭州,就有服裝電商負責人反映,“別人都不交,只有我交,不就吃虧了嗎?
存在重復性收費、設計不合理等問題
調研發現,企業家認為不合理的稅種,較多地集中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與房產相關的稅,這構成企業較大的成本困擾。企業家另一項不滿意的稅是企業所得稅。此外,征稅程序和稅制設計上存在的問題對企業的困擾超過稅率的影響,說明我國企業家對稅負的感受沒有停留在直觀層面,而是看到稅率之外其他因素的影響。許多企業家表達了對未來我國稅制法治化的較高期待。
另一個現象是,營改增對企業本是個利好,但有部分企業表示,稅負不減反增。在調研的企業中,有57家企業經歷了營改增變化,其中有36家反映稅負提高了。
反映營改增后稅負提高的企業,主要分布在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保險業、醫藥行業、農產品(12.790, -0.17, -1.31%)加工業、住宿和餐飲行業等。主要原因是部分行業進項稅額難以取得、融資成本不允許抵扣進項稅額、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稅款抵扣環節未能打通、金融商品年末買賣價差不允許結轉下一會計年度,以及稅改后出現稅負疊加現象,導致稅負結構不合理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企業負擔。
還有企業家抱怨“五險一金、殘保金、水利建設金等的繳納”存在較大壓力,一些企業在沒有賺到錢的時候還要繳納稅收,便覺得很冤枉且失去納稅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糟糕的納稅體驗,也影響著企業家的納稅積極性。課題組成員張林分析實地調研的問卷結果時發現,24%的企業家認為與稅務部門交涉時間較長,44%認為需要向稅務機關支付非正常費用。某液壓設備公司負責人反映,2005年建廠時,一個小小質檢員,驗收完混凝土建筑就要拿走200~300元,而這樣一個質檢員每天要跑數十個工地。
李煒光用經濟學上的“死角損失”解釋建立輕稅結構的必要性。因為征稅,市場實現的消費者盈余和生產者盈余都變小了,大部分變成稅收交給了政府。另外,消費者和生產者還有一部分損失掉的市場盈余,政府本來可以拿到卻沒有拿到。這部分損失,經濟學上叫“死角損失”。有“死角損失”存在,所以我們的稅收來源不穩定,企業家預期不樂觀。因為只是生產者盈余損失掉了,企業還有活路,如果征稅過分了,就會出現“死角損失”,也就是生產者和消費者損失了,而政府也得不到。這時候經濟增長的前景就不樂觀了,這就是現在很多非公企業(大部分是民營企業)面臨生存難題、政府稅收下降居民收入卻難以提高、消費疲弱三重困境的主要原因。
李煒光說,“死角損失”是經濟學上的一個重要發現。現代市場經濟中,交易可以創造財富,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交易可以“無中生有”地增加財富,而現在由于稅收“死角損失”的存在,就是“無中生有”的反面,屬于“有中生無”了。
李煒光認為,如何在今后的稅制改革中更多地體現與市場經濟更加適應的輕稅思維,既不增加整個宏觀稅負的水平,也不增加企業稅負,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重大課題。